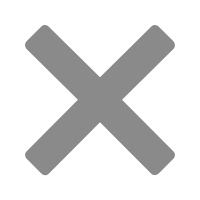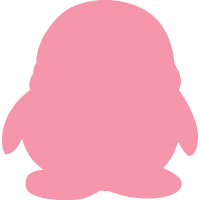第二章
有人爆出了当年我在巷子里和太妹扭打的视频。
视频掐头去尾,还给除我之外的人打了马赛克,整个视频呈现的就是我拿着木棍打一个瘦弱的女生。
许多自称我校友的人纷纷回应。
“我听过这件事,盛棉背靠着盛家,当年可跋扈了。”
“人家亲女儿回了家,她这个养女还不知收敛,带头霸凌别人。”
“我听我同桌说,她甚至差点逼得别人跳楼啊。”
“这个发虐猫贴的博主有点眼熟啊,好像也是个太妹,和盛棉关系很好。”
“虐猫贴的真实性有待考证啊,说不定是博主自己动的手呢。”
知宁家的地址很快就被找出来了,门口被人用血写着霸凌者去死,还收到了不少恐吓电话和短信。
更有甚者去盛家门口闹,现场直播让交出我的骨灰。
我缩在知宁怀里,看着直播画面。
我妈应该是不在家,盛木端出了新的骨灰盒,放在门口,云淡风轻地说:“任凭你们处置。”
盛心棠紧随其后,轻蔑地看了眼我的骨灰。
知宁催促着司机再快点,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
我的骨灰盒暴露在炎炎烈日下,被愤怒的人砸了一锤,再次碎了一地。
污秽泼上了碎片,和我的骨灰混在一起。
有人往上面吐口水,有人踩碎我的骨头。
我的灵魂感受到了剧烈的疼痛。
知宁蹲在在狼藉前面,不顾脏污,收起了我肉身的残余。
盛心棠出来了,居高临下地对知宁说:“马上中元节了,你烧纸问问盛棉,这样的结局她还满意么?”
我虚弱地躺在树荫下,心里无声地笑,满意,太满意了。
5
知宁把我的骨灰和豆包的东西放进了公墓。
她还往里头放了几包豆包爱吃的小鱼干,说:“小豆包以后要多来梦里看看姨姨和妈妈。”
我走过去,靠着墓碑趴下,上面刻了几个猫爪印。
写着豆包的生卒年月。
不知道它具体的出生日子,我就把相遇那天算作它生日。
而它死的那一天,是我新生的日子。
有陌生人在,我只能在心里默默喊它的名字。
可惜再也没有扬起蓬松尾巴的小猫回应,然后迈着优雅的步伐走向我。
知宁要带着我的亲子鉴定书再去盛家找我妈,我拦住了她。
“没用的,知宁。”
我生命最后的时光是在医院度过的。
托盛木的福,他向我公司施压辞退我后,我就病情加重进了医院。
我脸色蜡黄而瘦削,从镜子里看,眉眼间还是能隐约看见我妈的影子。
荒谬的猜想在我脑海中逐渐形成。
临死之际,我执意想验证这个猜想。
于是我同意了我妈一个人过来看我,并趁机收集了她的头发。
知宁拿着我和我妈的头发去做了检测。
看到结果的刹那,我心中坚信了多年的说法轰然崩塌。
原来我真的是我妈的亲女儿。
知宁带着亲子鉴定书去找了我妈,所有人都在。
知宁把亲子鉴定放在了桌上:“阿姨,我这次来是想告诉您棉棉的真实身份。”
盛木嗤笑一声:“怎么,盛棉都快要死了还想着让你帮忙使花招呢。”
他拿起报告,略微扫了几眼,没经任何思考,将它撕了个粉碎。
“这种造假的手段我见过成千上万例,我们不是三岁小孩。”
“我知道你和盛棉关系好,但我提醒你一句,她嘴里没有一句实话,你别被她骗了。”
知宁红了眼睛:“盛木你真混蛋!”
我妈问他:“那纸上是什么?”
我爸捡起碎片,和盛心棠对视了一眼,神色有些不自然。
他淡然开口:“不过是张伪造的亲子鉴定书。”
“对呀妈,盛棉不可能是我亲妹妹,当年您在场,亲眼看到了鉴定结果。”盛木劝她。
我妈眼神失了焦,脸上露出了凄惶和茫然。
盛心棠拉着她的手,宽慰她:“妈妈,虽然姐姐不是盛家的孩子,但是一直是您带在身边抚养,她生病了我也很难过。”
她垂眼,声音哽咽:“我回来后,这么多年她一直受到冷落,心里怨我很正常,我能理解。”
盛木不耐烦道:“棠棠,你别替她说话了,我看她就乐意见着家里为她闹成一团。”
我妈回过神来,对知宁说:“孩子,你去转告棉棉,即使她不是我的亲女儿,妈妈依旧很爱她,不要再撒谎骗人了。”
她这个人就是这样,耳根子软,没有主见。
一直过着优渥的豪门生活,年轻的时候靠着我外公,嫁人后听我爸的话,如今又对儿女言听计从。
“他们永远不会信我。”
知宁沉默了,然后艰难开口:“难道就这么算了,棉棉,我为你不值啊。”
“知宁,你把我高中的日记公开吧,还有那些照片。”
她微微一怔:“知宁那是你的伤疤……”
“最难堪的事情已经发生了,我还怕什么呢?”
6
我被扔下后,盛心棠或许是觉得家里没了我乐趣减半,她软磨硬泡说动我爸把我接回了家。
高一下学期,我从市郊的高中转到了和盛心棠盛木一所高中。
我是霸凌者的谣言也带到了那所高中。
盛心棠不再是刚回家那会儿怯弱自卑的小姑娘,她在高中积攒起了很高的人气。
追求她的男生受她挑唆,放学时带着一帮人将我拦住,带到了湖边。
那天恰好是期中考试前一天,我准备回家再复习复习。
男生推我入了水,但我小时候学过游泳,所以在呛了几口水后还是挣扎着爬了上来。
我浑身湿漉漉,他用脚踹向了我心窝,死死踩住了我扒拉岸边的手。
其余人将我的脑袋往水里按,快要窒息而亡时,他们又把我从水里捞上来。
我如同条死鱼被他们扔进了体育器材室。
身上的衣服被扒开了,我双臂护在胸前,拼命抵挡。
我有先天的气喘,爸妈为了锻炼我的身体,让盛木带着我参加了很多户外活动,所以身体强健了很多,但还是得定期吃药。
那药昂贵,爸妈之前买的药全吃没了,我又闷了水,此时大喘着气,头晕目眩,根本使不上力气。
身体最后道屏障被强行剥落,几道白光闪过,他们拍了照。
我呼吸越来越急和大声,喉咙里发出“嗬嗬”的声,他们可能怕事情闹大,匆忙逃走,临走前锁上了体育室的门。
我闭上了眼,过了好一会儿,残留的意识听见了屋外盛心棠和盛木的声音。
“妈心肠软,还让我带着盛棉回家,现在人也找不到,估计又出去鬼混了。”盛木语带刻薄地说。
“哥,姐姐不是那样的人,或许,”她顿了一下,“她先回家了呢。”
我身体费力往门口挪动,指望弄出点声响。
他们的声音逐渐远去,我眼角渗出了泪水,在地上一笔一划写着盛木的名字。
八岁的时候我差点走丢,盛木找到了我,他失而复得地告诉我:“棉棉,以后你遇到事情,就写哥哥的名字,并且在心里默念,哥哥就会来救你。”
后来我被巡逻的保安发现了。
我醒来后迎来的不是家人的关心,而是我爸的巴掌。
他面色铁青,骂我不要脸。
他还想给我一巴掌,被我妈拦下了:“棉棉差点就没命了,你这时候还怪她做什么?”
他深吸了口气,指着我恨铁不成钢:“我花大价钱买断了那些照片,那些照片要是泄露出去,盛家的形象和你的名誉就毁了,现在正是公司上升期,要不是你和那些男生乱搞,能出这种事情,自作孽不可活!”
“谁这么说的?”我咬牙切齿,声音因着刚醒发虚,“我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。”
我看向了盛心棠,她拎着保温壶,楚楚可怜地站在那儿。
盛木看不下去了,他哼了声,说:“你昏迷期间都是棠棠在照顾你,你还想诬赖她?”
我说的话苍白无力,没人听得进去。
妈妈掩嘴而泣,她失望地看向我:“棉棉你从前是个很乖的孩子,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呢?”
我拼命摇头:“我没有,妈妈,你相信我,妈妈……”
我妈随着他们离去,再也没有回头看我一眼。
我再次回到学校,名声更臭了。
有家长找上校长说我影响学校风气,希望把我开除。
校长忌惮我爸,还是留下了我。
他当着全校同学的面,通报批评我不知道检点,必须改过自新。
我在日记本上写下了好几页纸,浑浑噩噩,迈上了学校的天台。
盛木以前问过我长大以后想当什么,我指着天上的飞鸟说我想要变成鸟儿。
我在天台边缘晃荡着双腿,楼下的人行色匆匆,无人发现我的踪影。
被逼跳楼的人是我,被霸凌的人也是我。
可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,都没人相信我。
我的生命本该终结在那一天。
按键手机滴地一声,知宁用公共电话亭给我打了电话。
她说她从郊区骑自行车来找我了。
“棉棉,我来接你了,就在学校门口呢,去吃炒粉好不好?”她的声音有压抑不住的颤抖。
十六岁的盛棉怕那个女孩难过,于是收起了她的翅膀。
7
我将陈疴重新揭开,网络上的言论开始纷纷反转,却仍旧有很多质疑声。
不想再让知宁受我所累,我趁着她不注意溜出了屋子。
沿着草丛,我历经艰辛跑到了盛家的车库。
盛心棠的车还停在那儿,车门敞开着,人却不知所踪。
我藏在了副驾底下。
一阵争执声传了过来,我偷偷爬出来,看向了车库里头的电梯口。
盛木拽着盛心棠的手臂不放,一脸不可置信地说:“棠棠,你今天那通电话是打给谁的?是你给我虐猫的博文买的水军?”
“哥你放手,”她气急败坏地和盛木拉扯,“我说了我没有,我又不是盛棉,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情?”
“那你回答我的第一个问题。”他盯着她,目光中带了浓浓的审视。
“我是为帮你澄清。”她吞吞吐吐。
盛木显然不信,压抑着怒气说:“我还听到了你向爸要股份的事。”
盛心棠脸色唰地变白,盛木继续说:“你说你要百分之四十的股份,也就是说你想控股是么?”
她咬着唇,强行维持着冷静:“我控股怎么了,我也是爸的孩子,凭什么公司就要交到哥的手上?”
盛木难得朝她冷笑:“你在国外读的水硕,而且还逃课去夜店,爸妈捐了栋楼才给你换了毕业证书,你以为我不知道么?你对管理公司一窍不通,竟想着做管理层。”
“拿了百分之十的股份,每年的分红够你继续挥霍了。”
盛心棠红了眼:“哥,你变了。”
她随即准备进车里,我迅速藏回座位底下。
盛木声音抬高了:“棠棠,我是为你好!”
盛心棠死死抓住方向盘,一脚油门踩到底,不要命地冲了出去。
行驶在大道上,她眼底全是不甘心,边开车边自言自语:“要不是你是个男孩,爸的家产就全是我的,果然是一个妈生的,你一样惹人恨。”
我心里讶异了一下,原来她早就知道我是妈的亲女儿了。
她嘴角的笑越咧越大,畅意地笑出声:“那又怎么样呢,我妈是爸最爱的女人,他根本不爱那个老女人,他宁愿舍了盛棉,也要为我铺路。”
我全身像石化了般,凝滞在原地。
我的确曾经在我爸的书房发现过一张陌生女人的照片,但因为那时候太小,我爸第一次凶了我,就再也没进过他书房。
我不断地观察路上的情况,等路上车辆少了,她车速慢下来时,我猛地从车座下跳出来,抓住了她的头发。
盛心棠猝不及防地尖叫一声,用手疯狂推开我,慌乱中打反了方向盘,径直向路边的树撞去。
车子侧翻了,她满头是血,晕了过去。
而我身体小,很幸运,只受了点轻伤。
我忍着疼痛,用利爪深深地划破了她保养精致的脸。
交警过来开门时,我趁机跑了出去,藏在了灌木丛里。
我本想跟过去,被赶过来的知宁抓回了怀里。
“棉棉,我快要吓死了。”她忍不住哭了,想打我却又舍不得下手。
我轻声安慰她:“我这不是没事嘛,好知宁,我干了件大事,盛心棠毁容了。”
那些年因为我太阳穴留下的烟烫的疤痕,盛心棠没少冷嘲热讽。
她在纸上写丑八怪,贴在我身后,害我被全校人嘲笑。
她最爱惜自己的样貌,不知道这样的事情落在她身上,她会不会崩溃至极。
8
知宁给我简单包扎了几下,把我装进猫包,去了医院。
一向严肃的我爸像疯了一样问医生,我妈则差点晕了过去,盛木在旁扶住了她。
医生说盛心棠需要输血,告诉护士她是A型血,嘱咐护士带着人去血库调血过来。
我妈悲痛欲绝的表情突然变成了错愕。
她连忙抓住护士询问:“棠棠是什么血型?”
“A型血啊。”
她整个人像被抽干了灵魂,摇着头喃喃自语:“不可能啊,怎么可能是A型血。”
我冷眼看着这一切,她是O型血,我爸是B型血,不可能生出A型血的孩子。
可叹我妈养了我十二年,都没想着仔细看看盛心棠的血型,完全不顾念和我的情分,站在了她那边。
盛木仿佛也明白了什么,我妈神情激动起来,她问:“你和盛棉都是B型血对不对!”
盛木动作艰涩地点下头,我妈瞳孔一缩,眼神变得迷离而空洞,她的目光落在了我爸身上。
“盛子敬,”她声音颤抖地喊着我爸的名字,“我问你,棠棠,她究竟是谁的孩子?”
我爸此时顾不上难过了,眼见着瞒不下去,他瘫倒在长椅上,缓缓出声:“唐莹。”
“这么说,棉棉真的是我的女儿。”
她的手无措地停在了空中,眼睛瞪圆了,忽地又哭又笑,腿一软,坐在了地上,歇斯底里地喊叫。
“我做了什么,我做了什么?我养小三的孩子养了十多年,自己的女儿死后连骨灰都被人践踏!”
盛木脸上一下子没了血色,眉宇间涌上了极大的痛苦,他撑着墙,张着嘴,却什么也没说出来。
知宁看了我一眼,迈开步走向了他们。
她将亲子鉴定书放在了我妈的手里。
“这次,您亲自看看吧。”
她打开了我的日记,念着我不为人知又既为人知的过往。
9
“2005年6月1日,哥哥生病了,妈妈去医院陪他了,我也想去陪他,打针很痛的,哥哥说有我陪就不痛了,可是妈妈说医院有很多病菌,小孩子少去,我看见了流星,许愿哥哥病早点好。”
盛木的眼中全是悔意。
“2006年7月10日,我在木棉树下埋下了给未来的哥哥的礼物,他能找到吗?”
“2006年12月6日,妈妈过生日,我给她画了幅画,妈妈夸我画的很好,妈妈是我最亲爱的妈妈,希望她天天开心。”
我妈嘴唇哆嗦着,掩面哭泣,她声音沙哑,一声声喊着我的名字。
“2011年4月18日,生日宴上爸爸领回了一个小妹妹,原来我不是他们的亲女儿,可是我很感激爸爸妈妈,也很喜欢妹妹。”
“2012年6月10日,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害妹妹过敏的。”
……
“2015年4月4日,没人相信我,想死,但不舍得。”念叨这,知宁绷不住哭出了声。
盛木哀求知宁:“可以把棉棉的日记本给我吗?”
“你觉得呢?”知宁擦了眼泪,似笑非笑,“请问盛先生以什么身份索要棉棉的遗物?”
“我,”他张嘴,压抑着急促的呼吸,“我……”
“盛棉说,你曾经是她非常崇拜的哥哥。”
我妈迅速从地上起来,扑向我爸,又抓又挠:“盛子敬,都怪你,是你害死了我的棉棉,你把她还给我,还给我!”
知宁只是声音很轻地对她说:“阿姨,你冷眼旁观不顾盛棉死活的时候,有想过这一天么?”
她拎起猫包,带着我离去,将闹剧抛在了身后。
后来听说盛心棠发现自己毁容了,想不开就疯了,我爸把人送进了精神病院。
我妈和盛木往知宁的账户里打了一大笔钱,他们跪在门外,祈求再见见豆包。
然而屋里没有人,知宁早带着我去旅游了,去看海去漂流。
那是年少受原生家庭束缚的我们最大的理想。
在我的人生中,妈妈和盛木只是短暂地爱了我一下,但这样是有代价的,所以我为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
溺水过后气胸加剧,服药也加剧,等度过了大学四年,我的肺部已经到强弩之末了。
至于我爸,他或许从来都没真正爱过我,他重男轻女,好面子,又深爱初恋的孩子,我只是他的一个累赘而已,所以他才会费尽心思让我消失。
而我又很幸运,遇见了知宁和豆包。
与其说是我选择了她们,不如说冥冥之中,她们选择了我,并且拯救了我。
我依偎着知宁,一人一猫坐在海边看日出。
灿烂云霞中,海鸥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。
天空有飞鸟飞过,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
10盛木(番外)
我出生的时候,爸妈在门口种了棵木棉树。
两年后它第一次开出了红色绚烂的花朵,那天妈妈给我生了个妹妹。
妈妈说木棉的花语是守护,妹妹是木棉花,我是枝丫,我们彼此相依,彼此守护。
棉棉先天不足,母胎里带了病气,所以从小就身体羸弱,有支气管疾病。
附近的小孩喜欢欺负她,她打不过就喊我。
她穿着红色花袄,扎着两个羊角辫,摇摇晃晃地向我跑过来,小小的身板扑进我怀里,含糊不清地说:“的的,他们欺负我,你打回去。”
我更正她,是哥哥,她还是分不清“g”和“d”。
她五岁那年夜里发了高烧,爸妈那会儿出差了,家里只有两个佣人看着。
那夜我叫不醒人,只好自己背着棉棉去了附近的诊所。
佣人赶过来时,我忍不住哭了,因为生病的妹妹太脆弱,小小的一团趴在我背上,我一直害怕她就这么死去。
后来为了让她有个健康的身体,我带着她参加游泳、打乒乓球这些活动,她很聪明,学东西也很快,长成了个自信健康乐观的小姑娘。
她七岁时差点被拐走,小姑娘安全意识十分到位,镇定地带着人贩子拐到了少年宫,当时我刚好出来,就看见她飞奔向我,红着眼说她害怕。
我安慰她说以后遇到危险就写我的名字,在心中默念,我就会出现。
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无论她在哪儿,我都会尽量陪着她。
可是最终是我把她推入了绝望的深渊。
我爸在我十四岁的时候带回了个女孩,他说棉棉不是我亲妹妹,盛心棠才是。
那段时间我很迷茫,小太阳一样的棉棉怎么可能不是我的妹妹,我们长得那么像。
我爸说,时间久了,养女会越来越像养父母,即便没有血缘关系。
后来的亲子鉴定报告也越发让我认清了现实。
但我没办法割断和棉棉的情谊,我还像以前一样对她。
棉棉却逐渐变得让我不认识她了。
盛心棠说棉棉知道她猫毛过敏,我也记得当时谈这件事的时候棉棉似乎在现场。
血缘天然的亲近让我不知不觉地偏向了盛心棠。
我甚至听从了我爸的话,为了让她长记性,倒掉了棉棉的药,我侥幸地想,她现在身体好了很多,对药物的依赖性没那么强了。
我上高中后,学业逐渐忙起来,经常从爸妈那边听见棉棉很晚回家,我爸说估计是跟社会人出去混了。
有一天她浑身是伤地回家,我一下子就生气了,我气她怎么这么小就出去打架。
我爸要赶她出去,我也没拦着。
后来我实在担心,出去找了她,却发现她和另一个女孩子坐在一起吃东西。
她以前交朋友都会跟我说,现在心思深沉了不少。
我胡思乱想,恶毒地揣测她会不会生了别的心思。
再后来,棉棉又传出了霸凌别人的事,我质问她时,她只是反问我为什么不相信她。
于是我和她越走越远,将她扔在老宅,任由她高中被霸凌。
归根结底就是我当时听信了谣言,却从没想过去核实。
棉棉死前和我和她见的最后一面是在她的公司,她眼里已经没有了任何波澜,我一时心慌,冲动地打翻了她的纸盒。
看着她瘦削的脊背,我心中泛起了密密麻麻的疼,却还是压抑住帮她捡东西的冲动。
我欠她一句对不起。
因为猫伤了盛心棠,我还扔了她的猫。
那只叫豆包的猫被她养的很好,和棉棉一样可爱,其实棉棉不知道,我偷偷给它喂过几次猫条。
一步错,步步错。
我深陷在对她的错误认知中,将她的骨灰交给了别人践踏。
其实我早就发现了盛心棠的真实面目,只是碍于血缘一直忍耐和包容,结果她居然早就在谋划着抹黑我的形象,劝我爸让她控股。
真相大白的时候,我仿佛做了场噩梦。
我多希望棉棉没有死,她开心快乐地长大,回想起这些年她在盛家如履薄冰,谨小慎微地讨好我们,我就心如刀割。
妈说,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。
的确,无论是调换亲子鉴定的作为始作俑者的我爸,还是扮猪吃老虎的盛心棠,再到推波助澜的我和我妈,身上都承担着极大的罪孽。
我去了趟老宅,在木棉树底下挖出了棉棉说要送给我的礼物。
那是个铁盒,里头放了本笔画稚嫩的彩笔画,画的都是想象中她和我未来的生活。
最后一页的她变成了一只鸟,而我变成了一朵云。
“我自由地飞着,常常能看见哥哥。”
我哭的不能自已,将画册好好放起来,开车去了墓园。
墓碑上刻着“棉棉和她的崽豆包之墓”。
我眷恋地摸了摸墓碑,好像很久没有好好抱过她了。
刀割破了我的喉咙,血喷溅出来。
手机误触点开了今日头条的视频。
“盛家意外起火,一家三口尽数丧命。”
我好像看见了熊熊烈火,我妈捧着棉棉的相册大声地哭喊着:“棉棉,妈来陪你了。”
棉棉,哥哥也来陪你了,下辈子,让我们好好补偿你。
我微笑着闭了眼。